7月9日,薪火文旅实践团踏入殷墟博物馆。昨日在文字博物馆,队员们已从甲骨拓片与青铜铭文间触摸过文字演化的肌理,今日便循着这份对文脉的叩问,于殷墟博物馆展陈的脉络中继续探寻——那些铸于青铜、刻于甲骨的字符,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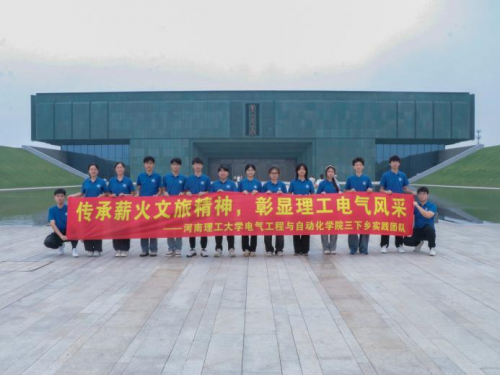
走进展厅,时光仿佛在此凝固。司母辛铜鼎稳稳伫立,纹饰间的饕餮纹在灯光下透着威严,仿佛仍在诉说着祭祀时的庄重;嵌绿松石刻辞骨柶上,松石与骨面交融出细密纹路,刻字在光影中若隐若现,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;“马危”折肩尊的器型古朴,腹部的铭文虽历经千年,仍能辨出当年铸造时的精心;小屯南地2172号甲骨平展在展柜中,上面的刻痕如同时光的密码,等待被破译;还有那铜手形器,指尖的弧度仿佛仍留存着主人的温度,铜钺的锋芒则透着当年的赫赫军威。队员们缓步穿行其间,目光在这些文物上流连,指尖轻抵展柜玻璃,仿佛能听见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——那是青铜冶炼的铿锵,是甲骨灼烧的轻响,更是文字初现时的郑重。

三楼特展的微光已在回廊尽头隐约可见。登至三楼,《子何人哉》与《长从何来》两大特展如双璧并立,在幽微的灯光中静静铺展。《子何人哉》展区中央,层层叠叠的甲骨如泛黄的典籍,承载着那位商代王子的“占卜日记”:“子其疫,弜往学?”的刻痕藏着少年的踟蹰,“舞戉卜左队吉”的卜辞透着演练的审慎,“妇好赠贝”的记录流淌着亲情的暖意。这些文字让“子”的形象从史简的模糊称谓中走出,成为可感可触的鲜活生命——他在“入”地的学宫研习祭祀之礼,在“舞戉”的实战中锤炼胆魄,更在与妇好的互动中流露赤子之心。相邻的《长从何来》则以亚长墓文物为骨,铜钺的锋芒、车马器的繁复,勾勒出军事贵族的壮阔人生。两展看似各呈风貌,实则以文字为经纬:王子的卜辞是个体生命的细腻注脚,亚长相关的铭文是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,一文一武,一微一宏,共同织就了商代文明的立体图景。

参观结束时,队员们望向展柜里的甲骨与青铜,那些刻痕仿佛仍在灯光下流转。“文心红旅”的意义,原是让三千年的文字在青年眼中苏醒——不是匆匆一瞥的过场,而是让文明的纹路,在凝视中烙进心里。走出博物馆,檐角的光影落在肩头,像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嘱托:这文脉的薪火,正等着我们续上光亮。(作者:徐浩然 徐一畅 徐海烽 方懿海 韩梓鑫)
免责声明:此文为转载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市场有风险,选择需谨慎!此文仅供参考,不作买卖依据。如有侵权或其他异议,请联系15632383416,我们将尽快处理。

